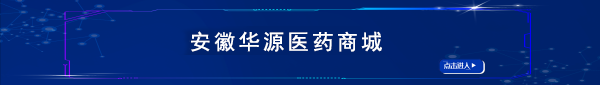“最近這幾年,來就診的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以下簡稱:AD)患者明顯比過去多了不少。”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莫明樹對39深呼吸說。他所在的廣醫一院神經內科每年接診的認知障礙患者中,多數都是AD患者, “可惜的是,他們絕大多數來到醫院時已經是中晚期了,這時候進行醫學干預,效果已經很有限。”
2025年1月3日,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5個部門聯合印發《應對老年期癡呆國家行動計劃(2024-2030年)》,該計劃提出預期在2030年,實現“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務的人群認知功能初篩率”與“認知功能初篩陽性人群干預指導率”≥80%的目標。該計劃的主要任務包括在基層開展老年期癡呆篩查與早期干預、提高老年期癡呆規范化診療服務水平以及宣傳老年期癡呆防控科普知識等等。
《行動計劃》的出臺,標志著我國首次對認知障礙的防控上升至國家層面,專家指出,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進程加速,未來20年,AD病患數量將呈指數級別上升。這不僅意味著巨大的醫療和社會資源消耗,也引發了對社區照護、養老機構建設和長期護理保險制度完善提出了巨大的要求。
“然而,在實際工作中,目前面臨諸多挑戰,醫生對于AD認知不足、診療設備缺乏、患者認知度低、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等問題,嚴重制約了AD在我國防控工作的開展。”莫明樹說道。

AD患者來醫院時,多數已到中晚期
7月6日,一對母女走進了診室。母親剛滿65歲,女兒劉鷗(化名)發現,母親最近這一年記憶力下降得特別快,剛完成的事情,轉眼就會忘記,說話也變得不利索。“由于我們在外地工作,讓母親一個人在家不放心,想在家里裝監控,但她的性格突然變得固執易怒,并不同意。”“我沒有問題。”聽到女兒的陳述母親在一旁大聲反駁,她有些緊張,眼神不自主的瞟向門口,這是在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神經內科副主任莫明樹診室內見到的一幕。
其實,這樣的病人還有很多,莫明樹對39深呼吸解釋,“人老了,忘記事沒覺得是大事。”這是許多老人來醫院時告訴他的話,但殊不知“遺忘”是阿爾茨海默病的核心表現,從忘記生活中的一件小事,發展到家中忘記關電源、煤氣,發展到忘記回家的路,最終忘記朝夕相處的子女,直至忘記“自己是誰”。
據劉鷗透露,并不是第一次發現母親的異常,在更早前,由于母親整晚睡不著覺,她曾帶母親在當地的小醫院就診過,甚至做了大腦“磁共振成像”(MRI),結果無異常,醫生開了些改善睡眠的藥物,母親覺得沒必要,最終也沒吃。“現在才知道,這也是阿爾茨海默病的早期癥狀之一。”

◎ 被藥監部門認可的AD確診手段僅有2項,一個是做腰椎穿刺取腦脊液,另一個則是做PET-CT。
《中國阿爾茨海默病報告2024》顯示,2021年,我國現存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及其他癡呆患者近1700萬,占全球患者的29.8%。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并不是每一個AD患者都能夠被清晰地確診為那1700萬分之一,“成為”患者之前,還有一段不斷確診之路。
“強調早期確診,是因為越早發現越有意義。“莫明樹形象地比喻,就像即將要熊熊燃起的大火,只能在它還處于小火苗的時候及時撲滅,才能避免損失。”在65歲的時候確診,那么70歲就處于早期認知障礙,生活能夠自理,再努努力,將病程中期延緩到80歲,雖然需要人照顧,但不會折騰人,等醫學干預到了85歲,老人還能和家屬聊天。
據悉,根據美國精神衛生學會《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的診斷標準。除了依據臨床表現、病程、病史,阿爾茨海默病的確診也依賴輔助檢查做“排除法”:腦電圖、核磁共振、血檢等等。如果有相關家族病史,患者還要做遺傳學檢查。一切順利的話,最快要一周才能確診阿爾茨海默病。
莫明樹解釋,但目前早期確診困難重重。一方面,輕度認知障礙階段,患者生活還沒發現明顯變化,中國患者對于疾病癥狀容忍度較高;另一方面,患者如果沒有通過臨床阿爾茨海默病評定量表(AD)量表篩查,想要確診需要通過PET-CT,檢查患者體內的β-淀粉樣蛋白(β-amyloid, Aβ)和Tau蛋白。但想做PET-CT并非易事。這需要專門的示蹤劑,而制作示蹤劑又需要對應的加速器,許多醫院的PET-CT用于檢查腫瘤,對阿爾茨海默病則無能為力。許多二三線城市的醫院缺乏精準確診的能力,莫明樹說,即便找對了醫院,因未被納入醫保,價格也成為了確診的門檻。“只要做就要七千多,相對比較昂貴。”
近年來,為了“更早確診”,醫生們也在盡力編織出一張覆蓋全社會的篩網,使更多存在認知風險的老人來到他們面前。2024年9月,阿爾茨海默病腦脊液系列試劑盒在瑞金海南醫院正式展開應用,并啟動真實世界研究。2025年6月,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研發的Memtrax認知篩查工具,可使AD干預窗口前移 5-10 年。今年,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針對診斷疑難AD的診斷,也推出了基于AV45探針的PET-CT,并啟動惠民減免項目;同時,針對AD的廣泛篩查,也開發了“AI+書寫”智能早篩設備,已在進行臨床試驗。
有效的治療藥物仍然不夠
時至今日,醫生們仍不清楚阿爾茨海默病的病因和發病機制。
這也使得AD藥物研發靶點的選擇充滿不確定性。據39 深呼吸了解,目前全球藥企已在該疾病上投入了上千億美元,卻鮮有人能真正打開那扇門。多項研究表明,這一領域的新藥研發失敗率超過90%,遠高于癌癥藥物的研發失敗率。因此,也被業內形象地稱為“研發黑洞”。
而最近,我國獨有的兩項AD治療手段被禁用,更是將這一疾病的治療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2019 年,國家藥監局有條件批準我國自主研發AD藥物“九期一”上市后,今年因臨床療效和作用機制為未提供有效數據,未獲得“完全批準”,藥物已經停產。
而在7月8日,國家衛生健康委網站發布通知,禁止將“頸深淋巴管/結—靜脈吻合術”(LVA)應用于阿爾茨海默病治療。
據悉,LVA最初被用于治療淋巴水腫,浙江省人民醫院手外科原主任、杭州求是醫院院長謝慶平首創將其用于阿爾茨海默病治療。此后數年,LVA手術闖入了阿爾茨海默病家屬的視線,逐步成為了醫療界的“網紅手術”,直至此番被禁。
與“九期一”停產理由相似,國家衛健委明確表示,已組織專家對該技術進行評估,該技術應用于AD治療尚缺乏相關臨床前研究的直接證據,該技術處于臨床研究早期探索階段,適應證及禁忌證尚不明確,其安全性、有效性和經濟性缺乏高質量循證醫學證據和衛生經濟學證據。

◎ 很長一段時間,對于AD患者來說,在缺乏有效藥物治療的前提下,只能選擇手術治療。
莫明樹介紹,早期AD藥物都是對癥治療,包括多奈哌齊、卡巴拉汀和美金剛。這些藥物在一定時期能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減輕精神行為癥狀,但并不能改變疾病的進程,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疾病的發展變化進程和結局,因而在療效和延緩病程上具有局限性。“就像一輛開往懸崖的列車,藥物只能減慢列車行駛的速度,卻無法更改它的宿命。”
隨著對AD研究的不斷深入,β淀粉樣蛋白(以下稱“Aβ”)斑塊和Tau蛋白纏結是阿爾茨海默病的兩個關鍵病理特征,相關假說也成為科學界試圖解釋發病機制的主流理論。
在此基礎上,有二款單抗藥物侖卡奈單抗和多奈單抗在近兩年內分別在我國獲得批準,劉鷗的母親也因為發現得及時,早早使用了多奈單抗的治療。兩個藥物都有扎實的臨床數據,都是通過清除腦內淀粉樣斑塊來延緩疾病進展,達到治療目的。在莫明樹看來,這兩種藥物的特殊意義是,“多年來終于證實了Aβ假說在臨床上的可行性,明確能夠清除腦內淀粉樣蛋白,并且可以延緩認知能力的下降。”
但目前,對于阿爾茨海默病的治療手段依然匱乏。盡管新型的靶向藥物為該疾病的治療帶來希望,且不說新藥價格昂貴,一年藥費動輒十幾二十萬讓很多家庭無力承擔,即便吃得起,這兩個藥物也主要用于早期AD的治療。
對于大多數首診就已經進入中晚期的AD患者,仍然缺乏特效治療手段,許多家庭不得不尋求其他治療方法。
照顧AD患者,家屬覺得很難
確診半年后,王宇與父親的交流只剩下“是”、“好”,少了完整的句子,多了肢體語言和猜測。再后來父親大小便失禁,家中又多了幾個壁掛式小便池,還附上“老爸請到廁所上廁所”之類的提示語。父親能念出這些字,但無法理解。褲子經常又濕又臭,他起初非常煩躁和憤怒,一度認為父親是故意的。
每次洗澡都一地狼藉,廁所亂糟糟的,父親僵在那兒不動,王宇崩潰時沖父親喊出:“把你送到養老院去!”這是一句氣話,但他確實需要人幫助。“我也想過請保姆,但人家一聽說要照顧老年癡呆的老人,就不愿意上門了。”
一旦AD進展到中重度,不僅藥物的療效非常有限,家庭的照護壓力是成倍增加。有數據顯示,在我國AD的主要家庭照顧者的年齡為45歲,他們多為患者的配偶或子女。2024年發表在《BMC Geriatrics》的一項研究顯示,中重度阿爾茨海默病的總成本是輕度的1.3、2.1倍。患者往往從失智發展到失能,需要家人辭去工作,做7x24全天候的照料。
有家屬這樣傾述:“為了照顧患病的母親,自己辭去了工作,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陪伴,換來的是母親的不滿、怨恨和冷漠,最后我都覺得我會在她面前先去世。”更有甚者,在無計可施下,用上了不正規的治療,靠給老人戴上約束手套,用繩子綁住,來換取短暫的安寧。
除了身心的高壓負荷,還有更現實的壓力,那就是巨大的費用開支。
一項2022年發表在《eClinicalMedicine》的研究計算了阿爾茨海默病帶來的全球經濟負擔。其預計,在2050年,中國將是阿爾茨海默病和其他相關癡呆癥經濟負擔最高的國家,達到8.7萬億美元,是第二名美國1.4萬億美元的六倍以上。
莫明樹強調,阿爾茨海默病不單單是影響患者健康的兇手,更是摧毀整個家庭和睦幸福的隱形炸彈。

◎ 現在中國大部分養老機構不會甚至不敢照顧AD老人,一方面是照顧風險高,一方面是收益成本不對稱。
中國老年保健協會阿爾茨海默病分會發布的首個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家庭生存狀況調研報告顯示,65.43%AD患者的照護者感到心理壓力大;68.69%的照護者健康受到影響;78.39%的照護者表示社交生活常受到影響。阿爾茨海默病的家庭照護者身心長期承受巨大壓力,社會支持資源短缺,標準化、規范化的臨床診療和人性化的照護康復需求遠遠未被滿足。
“AD照護是全方位、全天候、全病程的照護,這是與其他慢病照護最大的不同。而且這個照護的過程費心費力費神。”中國老年保健協會阿爾茨海默病分會主任委員解恒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而《應對老年期癡呆國家行動計劃(2024-2030年)》的兩項主要任務正是增加癡呆老年人照護服務供給及構建老年期癡呆友好的社會環境,包括到2030年,100張床位以上且具備相應服務能力的養老服務機構中,設置癡呆老人照護專區的機構要超過50%。
然而,行業人士表示,一些以托老為主的低端養老院出于經營壓力,建設的意愿較低,中高端養老院可能對于認知照護專區的建設更加積極,但收費并不親民。
39深呼吸實地采訪了廣州一家規模較大的民營養老機構,發現對于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定位高護理級別,入住首先要支付押金10萬,房費每月8000-9000元,護理費用每月3000-13000元不等,這對于一個普通家庭而言,這樣的費用太高了。
近年來,各地方各相關部門都在持續關注認知癥老人的照護難題。2016年被稱為社保“第六險”的長期護理險開始在我國15個城市試點,2020年9月,試點擴大到49個城市(區)。
保險內容顯示,失能狀態持續6個月以上,經過醫療機構或康復機構診療、評估即可參保。長期護理保險基金主要用于支付基本護理服務所發生的費用。
但從目前《2023年全國醫療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3年,享受長護險待遇人數共134.29萬。而據民政部2024年9月的數據,國內失能老人約3500萬,享受到長護險服務的老人尚不足5%。
有媒體報道,多家連鎖運營的養老機構負責人員都表示,國內失智老人的照護,仍面臨“一床難求”的局面。以廣州為例,2023年以來在廣州各醫療機構就診60歲以上診斷為癡呆相關疾病的老年人數為12200人,而認知障礙照護床位僅1967張。
絕大多數“王宇們”,目前只能靠自己和家庭,赤手空拳地面對家中最熟悉的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