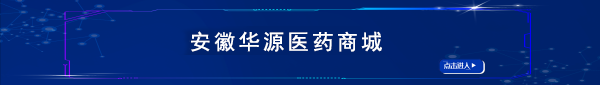論及近幾年的創新藥發展的兩大模式,那必定是First-in-Class與Fast-Follow。
前者是創新藥源頭創新的最高模式,不僅對企業技術要求、研發周期、研發成本都有較高的要求,并且不確定性與失敗率均較高,但同時也是新藥領域收入最高的存在,總體上是風險與收益并存的存在。
后者則是對FIC產品的快速跟蹤,在避開專利風險的同時,對新藥分子進行改造與修飾,試圖在有效性、安全性上做出差異,但本質上的作用機制仍與FIC產品相同或相似,對比FIC產品,其成藥性方面大大提高,能快速實現價值變現,是當前國內絕大多數創新藥企很誠實的一個選擇。
當然,Fast-Follow也存在極大弊端,其中最突出一點即策略之下的藥物靶標與適應癥大量重疊,資料顯示,國產新藥靶點集中度從2018年的18.3%逐年提升至2023年的27.1%。

圖片來源:東吳證券研報
新藥研發作為一項技術風險、市場回報與臨床需求的復雜博弈,原則上講,無論是Fast-Follow還是FIC,其本質上并非對立關系,而是藥企在不同發展階段的一種戰略工具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Fast-Follow可快速積累技術與市場經驗;而FIC則是實現長期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只顧著抄作業容易陷入同質化泥潭,而一味追求FIC的企業也更容易“夭折”,理論上唯有平衡創新與風險,方能在全球生物醫藥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
事實上,眾多Biotech藥企在經歷近幾年Fast-Follow經驗積累后,部分企業已經開始嘗試向“新靶點與新靶點組合”方向轉變,這一點通過國產ADC在全球領域的地位就可明顯看出。
20款
國產ADC領先全球
據藥智數據顯示,全球范圍內針對ADC藥物(排除PDC、RDC等新偶聯技術),海外藥企在靶點上的優勢正在喪失,與此同時部分國產藥企在ADC新靶點與新靶點組合方面卻逐漸占據了領先地位。
不完全統計,目前全球范圍內的ADC靶點超過40個,海外藥企優勢靶點在20個以上,占比約50%,國內藥企優勢靶點約20個,占比同樣在50%,整體呈現勢均力敵的局勢,并且較過去幾十年,海外藥企一家獨攬的情況而言,已大有改善。
部分國產ADC優勢靶點與領先企業

數據來源:藥智數據
其中,根據最高臨床階段排序,CLDN18.2與VTCN1兩個靶點的海內外差距最大,國產ADC在該領域的最高臨床階段已處于臨床Ⅲ期,不出意外CLDN18.2與VTCN1兩個靶點的全球首款新藥將誕生在中國。
同時,除了上述海內外均有布局的經典ADC靶點(國產Biotech反超登頂),領域內也有不少以國內Biotech為起始的創新靶點(或首次應用于ADC領域),比如以康諾亞CM518D1為領先的CDH17-ADC藥物、以華奧泰生物HB-0052為領先的CD73-ADC藥物、以樂普生物MRG006A為領先的GPC3-ADC藥物等。
傳統靶點代表:
CLDN18.2 ADC的魅力
緊密連接蛋白(Claudin,CLDN)在鄰近細胞間可形成緊密通道,調控離子、溶質等物質流通。Claudin18(CLDN18)是胃上皮細胞中緊密連接的主要組成部分,CLDN18具有CLDN18.1和CLDN18.2這2種亞型,其中CLDN18.2在胃癌、食管癌等惡性腫瘤中特異性高表達,且腫瘤細胞因增殖快、易侵襲轉移等特性喪失緊密連接結構,導致其表面的CLDN18.2分子表位更易暴露出來。據文獻報道,胃癌中Claudin18.2表達率在42%~86%左右,胰腺癌中陽性率高達60%,其高表達特異性使其成為胃癌或其他腫瘤靶向治療的潛在大靶點。
2024年10月,安斯泰來的Claudin18.2單抗Zolbetuximab作為全球首款Claudin18.2靶向藥獲FDA批準上市,過程雖一波三折,但好在為該靶點領域開了個好頭,而目前Claudin18.2雖非嚴格意義上的新靶點,但其在雙抗、ADC等領域卻尚無任何一款新藥上市,故在上述領域中,其靶點產品仍多為FIC產品,尤其是ADC。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超過20款CLDN18.2 ADC在研,最高階段已至臨床Ⅲ期,并且所有該臨床階段產品均為國產新藥,包括石藥中奇的SYSA-1801、恒瑞的SHR-A1904、康諾亞生物的CMG901、信達生物的BI-343、禮新醫藥的LM-302。
全球CLDN18.2 ADC在研管線情況

數據來源:藥智數據
顯而易見,就Claudin18.2 ADC領域而言,國產管線地位強勢,已極大地領先于海外藥企,而這樣的局面則是國內政策支持、地域優勢與資本助力等多重因素協同作用的結果。
因素1:地域優勢
一直以來,新藥研發與市場需求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關系。市場需求驅動新藥研發的方向和速度,而新藥研發的成果又反過來滿足并引導市場需求的變化。
而對比海外市場,國內Claudin18.2 ADC領域發展迅速的首要原因也正是其天然的地域優勢。

數據來源:《2022全球癌癥統計報告》
《2022全球癌癥統計報告》內容顯示,中國胃癌發病例數和死亡例數分別占全球胃癌發病和死亡的37.0%和39.4%,患者基數龐大且治療需求迫切。傳統化療與PD-1療法對晚期患者效果有限,三線治療中位生存期僅約半年。這種未滿足的臨床需求促使國內藥企優先布局胃癌市場,CLDN18.2 ADC在中國區域崛起也屬于常理。
因素2:資本助力
眾所周知,任何一個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都離不開資本的長期投入和澆灌,而國產Claudin18.2-ADC快速發展的又一關鍵因素也正是“資本支持”。一者,外部層面,全球關于CLDN18.2 ADC的BD交易數量也呈現出一片大好的局面,過去兩年有不低于5起BD交易圍繞其展開,甚至整個CLDN18.2領域近兩年囊括超25起交易,涉及總金額近150億美元,國產CLDN18.2 ADC正是其中主要標的。
2022年5月,Turning Point以超過10億美元的總價獲得禮新醫藥LM-302的部分開發及商業化權益。
2022年7月,科倫博泰就SKB315與默沙東達成合作及獨家許可協議,交易總額超過9億美元。
2023年,樂普生物/康諾亞以11.88億美元將CLDN18.2 ADC產品CMG901授權給阿斯利康,使得樂普生物2023年業績成功扭虧。
2023年10月,恒瑞醫藥宣布與默克就其自主研發的SHR-A1904達成獨家許可協議,潛在交易總額高達14億歐元。
內部層面,一方面如石藥集團這樣的大型企業中,將Claudin18.2-ADC項目放在石藥中奇承擔著戰略品種研發的使命的子公司,至少在研發資金上的支持絕不會差。另一方面,如禮新醫藥這樣的Biotech企業,過去多次融資的目的均是用于加速LM-302的臨床進度推進,可以說,絕大部分禮新醫藥股東對企業的資本認同都來源于這款ADC產品。
因素3:政策支持
當然,國內CLDN18.2 ADC領域的快速發展也離不開政策的扶持,一方面國家藥監局為ADC藥物開設特殊審評通道,加速審批,另一方面多款Claudin18.2 ADC被納入突破性治療品種,進一步縮短了研發周期。

圖片來源:藥智數據(點擊查看大圖)
新興靶點代表:
CDH17
如果說CLDN18.2是ADC領域前幾年爆火的靶點,那么今年AACR大會上十數個管線集中釋放數據的CDH17 ADC就是CLDN18.2的繼承者。
CDH17,也稱為肝腸鈣粘蛋白,是鈣依賴性蛋白質CDH超家族的非經典成員。其主要在腸上皮細胞及部分胰腺導管上皮細胞中表達,健康成人的肝細胞、食管和胃黏膜中幾乎不表達。研究表明,在胃腸道腫瘤,CDH17在超過50%胃癌、90%~95%結直腸癌、53%膽管癌,50%胰腺癌及部分肝癌中表達,且其表達水平與患者的預后和治療反應密切相關。

數據來源:三優生物
作為新興治療靶點,CDH17靶點領域尚無任何一款新藥上市,且單抗、雙抗、CAR-T、ADC等多賽道并行,其中ADC與CAR-T是目前在研進度最快的兩個技術方向。
據藥智數據顯示,目前全球范圍內有超20款CDH17 ADC藥物在研,并且其原研企業幾乎都是國產Biotech,目前僅5款進入臨床階段,分別來自康諾亞(CM518D1)、宜聯生物(YL217)、翰森(HS-20110)、普眾發現(AMT-676)和TORL Biotherapeutics(TORL-3-600)。
全球CDH17 ADC臨床階段管線

數據來源:藥智數據
以目前HER2與CLDN18.2賽道等ADC賽道的擁擠情況來看,CDH17 ADC的競爭格局無疑是相對寬松的,而且以目前CDH17 ADC在臨床前和一期臨床均展現出巨大的潛力,未來國產藥企極可能借此靶點揚名海外。
其中,美雅珂生物的MRG007與康諾亞生物的CM518D1是目前最有希望率先獲批的CDH17 ADC,各自差異化的設計也讓其有望成為顛覆消化道腫瘤治療的存在。
雙抗ADC:
1+1>2的奧秘
在傳統ADC通過單克隆抗體將細胞毒性藥物靶向遞送至腫瘤細胞,實現對腫瘤的精準打擊的理念得到初步的臨床驗證之后,腫瘤異質性和耐藥性等問題也同樣隨之而來,一者腫瘤細胞的異質性使得單一靶點的ADC難以覆蓋所有腫瘤細胞,導致部分腫瘤細胞逃逸治療;二者長期使用ADC藥物會誘導腫瘤細胞產生耐藥機制,降低治療效果。
因此,為了應對上市技術局限性,雙抗ADC隨之誕生。首先,機制上雙抗ADC的雙靶點特性能夠增強對腫瘤細胞的特異性識別和結合能力,提高腫瘤細胞對藥物的攝取效率,一般而言首選信號通路密切相關的兩個靶點,如EGFR+c-MET、TROP-2+PD-L1,可有效發揮協同抗腫瘤作用,最終導致產品治療效果大幅提高。
而事實上,在雙抗ADC領域,國產新藥的領先程度甚至還超越單抗ADC。
部分雙抗ADC的管線數據

數據來源:藥智數據(點擊查看大圖)
目前,雙抗ADC領域在雙表位ADC與雙靶點ADC兩個方向均有布局,以較為成熟的HER2與c-MET靶點為例,前者上正大天晴的TQB2102、軒竹生物的XZP-KM501均可以同時靶向ECD2和ECD4兩個HER2表位;后者上康寧杰瑞的JSKN-016,則可同時靶向HER3和TROP 2兩個相關靶點,誘導TROP2和/或HER3陽性的腫瘤細胞凋亡,疊加作用可以有效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
展望:
新藥從來不是一片坦途
當然,國產藥企除了在新靶點ADC與新靶點組合ADC方面位于全球頂流之外,其實在其他偶聯相關領域內同樣具備潛在優勢,ADC領域的創新方向也并不局限,比如諸多更新穎、更具想象空間的產品正在逐漸誕生,比如今年AACR大會上爆火的雙毒素ADC就是最好的代表。
雙毒素ADC作為ADC技術領域的又一創新突破,近年來吸引了眾多科研人員和藥企的關注。其作用機制是在同一抗體上偶聯兩種不同作用機制的細胞毒性藥物,通過雙毒素的協同作用,實現對腫瘤細胞的多維度、協同化殺傷。這種獨特的設計理念旨在克服單毒素ADC在治療過程中可能出現的耐藥問題,提高藥物的療效和持久性。
2017年,Levengood等人披露了首個雙載荷ADC,該ADC在含有正交保護的半胱氨酸殘基的短肽連接體上偶聯MMAE和MMAF,DAR為16(8+8),使全世界首次對雙載荷ADC有了基本概念。
2018年,Kumar等人報道了第二個雙載荷ADC,在傳統MMAE+MMAF的組合之外,有了MMAE+PBD的全新構成,打開了雙載荷ADC的想象空間,同時該研究中還重點提及了其合成的分支Linker,為后續更多雙抗ADC的誕生點明了要點。
2021年,德克薩斯大學休斯敦健康科學中心的Kyoji Tsuchikama課題組通過點擊化學方法成功構建了均一的雙載荷ADC,使得DAR組合更加靈活(2+2,4+2和2+4)。
2023年,繼同一連接子上偶聯不同的載荷之后,通過模塊化設計,將兩種不同的細胞毒性藥物(Payload)分別偶聯到抗體的不同位點,從而實現多機制協同作用,擴寬了雙載荷ADC領域的概念。
2025年,AACR大會,多禧生物、親和力生物、康弘藥業與康寧杰瑞四家國產Biotech相繼公布了其雙載荷ADC的最新臨床數據。
2025年,繼諾華躬身入局開發雙毒素ADC之后,國內宜聯生物、信達生物、康寧杰瑞、普米斯、啟德醫藥也相繼擁有了在雙毒素ADC上的系列布局。
其中,康弘藥業開發的TROP2雙載荷ADC藥物KH815,已成為全球首個進入臨床階段的雙毒素ADC藥物,KH815以TROP2抗體hRS7為骨架,搭載了拓撲異構酶1抑制劑和RNA聚合酶Ⅱ抑制劑兩種有效載荷。拓撲異構酶1抑制劑能夠抑制腫瘤細胞DNA的合成和修復,導致DNA斷裂,從而阻止腫瘤細胞的增殖;RNA聚合酶Ⅱ抑制劑則主要作用于腫瘤細胞的RNA合成過程,抑制mRNA的轉錄,進而阻斷腫瘤細胞蛋白質的合成,從源頭上抑制腫瘤細胞的生長和存活。這兩種毒素作用于腫瘤細胞的不同生物過程,形成了強大的協同效應。
很明顯,該療法研究雖誕生于海外,但以目前局面來看,未來其成功或許還將被國內藥企實現。
小結
總體而言,國產藥企在ADC領域正展現出令人矚目的創新活力和發展潛力。
傳統ADC方面,國產藥企在HER2、EGFR等傳統靶點上雖未占到優勢,但卻在系列創新ADC靶點上占據了初步優勢,比如CLDN18.2、CDH17與CD73等靶點ADC的頭部企業均為國產藥企。
雙抗ADC方面,國產藥企的研發進度迅速,全球研發階段靠前的雙抗ADC幾乎都是國產新藥,且無論是雙表位ADC、雙靶點ADC均已領先全球,如EGFR+c-MET、TROP-2+PD-L1。
雙毒素ADC方面,繼諾華躬身入局之后,國內已有十數家藥企披露了相關布局,其中不僅有康寧杰瑞、宜聯生物這樣的Biotech企業,更有信達生物這樣的Bigpharma,甚至康弘藥業的KH815已成為全球首個進入臨床的雙毒素ADC。
如今,國產藥企從對傳統熱門靶點的深耕細作,到在新興靶點上的搶先布局;從雙抗ADC的突破性進展,到雙毒素ADC的前沿探索,中國藥企正以多元化的創新策略在全球生物醫藥競爭中嶄露頭角。
其背后,一方面是由于地域優勢帶來的龐大患者基數和未滿足的臨床需求,為國產ADC的研發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資本的持續助力,為創新藥物的研發注入了強大動力,(當然要想得到資本的認可,基礎的成就仍須具備);最后加上政策的積極扶持,再為藥物研發和上市開辟了綠色通道。
三者共同助力之下,國產ADC產業想不快速發展,領先全球都難!
當然,新藥研發之路從來都不是一片坦途,盡管國產ADC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仍面臨著技術挑戰、市場競爭等諸多考驗。未來,國產藥企需繼續堅持創新驅動,平衡好創新與風險,不斷探索ADC技術的新邊界,以更加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扎實的臨床研究,推動更多優質ADC藥物走向世界。